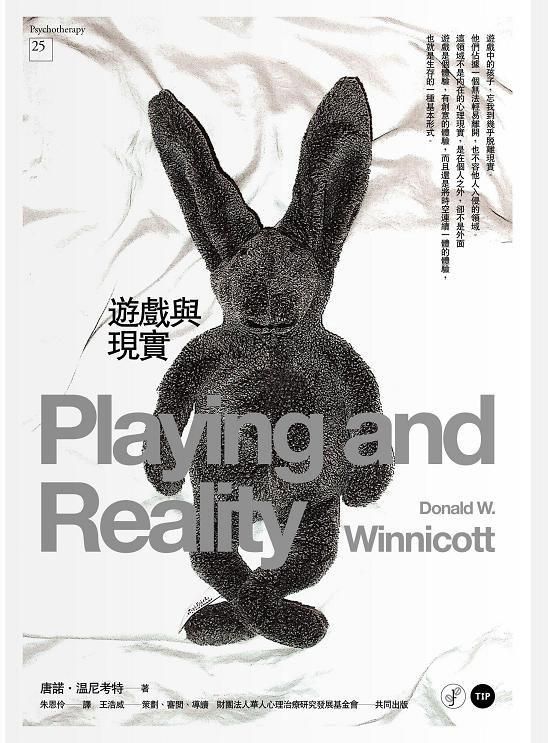文|唐諾.溫尼考特
譯|朱恩伶
不要把這個字眼侷限在
成名的或廣受讚揚的傑出「作品」這個狹窄框框裡,
而能把它擴大來指「面對外在現實時,興味盎然的生存態度」。
有創造力的感覺比甚麼都更讓人覺得「人生是值得活下去的」。
跟這種生活態度恰恰相反的,則是對外在現實百依百順的順從關係,在這種關係裡,我們必須努力融入或費力去適應外界的大小事宜。因此,對個人來說,對現實的逆來順受,有種白忙一場的味道,而且還連帶著一種消極的想法,彷彿一切都無所謂,人生也不值得活。令人乾著急的是,在這當中許多人至少都還體驗過富有創造力的生活,也曉得自己大部分時間其實都活得毫無創造力,彷彿牢牢的被困在別人的創造力裡頭,或是身陷在機械化的運轉之中。
從精神醫學的角度來看,上述第二種逆來順受的生存方式,是一種病症。
從某方面來說,我們理論上相信,
活得有創造力是健康的,而一味的順從現實,
則是有病的癥兆。
我們的社會普遍存在的態度,以及時代的哲學氛圍,無疑助長了這個看法;這是我們在此時此地特有的看法。換個地方,或換個時代,我們的看法可能會大不相同。(延伸閱讀:「陪我玩演戲的遊戲! 」角色扮演遊戲對孩子的發展至關重要)
活得有創造力或毫無創造力,這兩個選擇之間的對比宛如天壤之別。假如不論在任何情況下,我們都能在這兩個極端中選擇一個的話,那麼我的理論可能會更容易了解。但是,從個別差異的角度來談外在現實時,我們所仰賴的客觀程度也不一,所以這個問題就變得曖昧難解。在某個程度上,客觀是個相對的說法,因為客觀認知的事物,在定義上,多少也是主觀的想像。這雖然是本書鎖定的討論範圍,但是我們也得注意,對許多人來說,外在現實多少還是個主觀現象。在極端的案例中,某些人的虛幻錯覺會在特殊時刻或一般情況下產生。關於這種狀態我們有各式各樣的措辭(「垂死的」、「心不在焉的」、「不切實際的」、「不真實的」),在精神醫學上,我們把這種人稱做「類分裂」。
我們曉得,這種人在社群裡有他們的價值,他們可能過得很快樂。不過我們也注意到,對他們來說,生活可能也有某些困難,和他們一起生活的人,尤其會有這種感覺。
他們可能會主觀的看待這個世界,
容易產生妄想,或者在大部分領域可能很篤定,
在其他領域卻受到一個妄想系統的影響,
要不然就是在身心關係(psychosomatic partnership)方面,
結構可能並不穩定。
所以我們可以說,他們的協調配合能力很差。(延伸閱讀:小兒職能治療師眼中的重點發展—1歲以前寶寶要學會的事!)
有時候生理上的障礙,好比視力或聽力缺陷,也會推波助瀾,讓問題變得更加混淆,使我們無法清楚的區分,究竟是虛幻的錯覺,還是生理異常的殘障。這種形勢如果發展到極端,就是我們所謂的,在精神病院被貼上精神分裂症標籤的病人,不論他們的症狀是暫時的還是永久的。
本文摘自《遊戲與現實》
你可能還會想看…
別要求孩子活的順從乖巧,因為快樂的泉源來自活出富創造力的人生(下)
「當我需要做自己的事,孩子又黏著我怎麼辦?」—專家建議用這3個方法培養孩子獨立遊戲的能力。(上)
「在孩子遊戲時需要適時放手, 讓孩子盡情探索。」—為什麼進行緊張刺激的遊戲如此重要?
作者介紹
唐諾.溫尼考特(Donald W. Winnicott, 1896-1971)
1896年四月七日生於英國普利茅斯。1914年進入劍橋大學耶穌學院,在結束戰時服役後,又到倫敦的聖巴瑟洛繆醫院繼續研習醫學,並於1920年取得執業資格。
溫尼考特醫師的醫療生涯從小兒科開始,在接觸了精神分析後,愈來愈深入地研究兒童心理學。他在幼兒發展理論上的貢獻享譽國際,備受推崇,其中最為人津津樂道的,莫過於所謂「夠好的母親」(good enough mother)、「過渡性客體」(transitional object)、「真我∕假我」(true self / false self)以及治療情境中的「扶持」(holding)等概念語彙。這些充滿創意、令人嘆為觀止的洞見,奠基於豐富的臨床工作經驗,特別是他與母親、小寶寶和兒童之間的互動。
教授兒童精神醫學及進行精神分析超過四十年的溫尼考特醫師,曾擔任英國精神分析學會主席、皇家醫學會小兒科部門主席,以及英國心理學學會內科部門主席等職務。他經常在精神分析和醫療期刊上發表文章,也常常向許多職業團體講授兒童發展,對象包括教師、助產士、父母、社工人員、地方法官、醫師、心理分析學者以及精神科醫師。著名的代表作則有:《從小兒醫學到精神分析》、《孩子、家庭與外在世界》和《遊戲與現實》等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