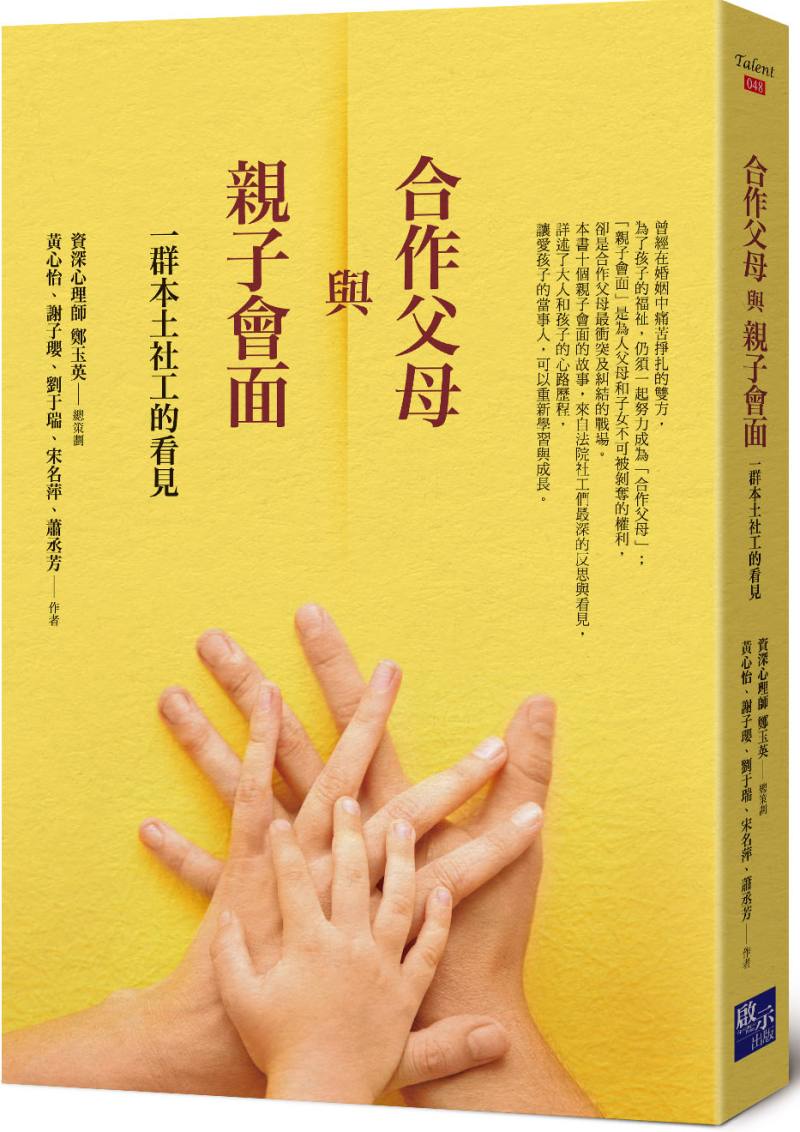作者|黃心怡、謝子瓔、劉于瑞、宋名萍、蕭丞芳(現代婦女基金會社工團隊)
「離婚後重新練習一起當家長。」—保持交集、成為合作父母其實是為孩子留一條路(上)
為孩子留一條路
雖然很期待我們可以變成平行線、不需要交集、互動,但有時候碰到不得不溝通的議題,像是需要討論小孩寒暑假安排、補習費用……,難免又弄得不愉快。
雖然我們盡量避免在孩子面前吵,但回家後我還是會忍不住講幾句「你看,你爸就是這麼難溝通、根本就不替別人著想」、「你爸就是不想幫你付錢」……。
「青春期之後」孩子有很大改變。孩子幾乎從來不在我面前談他爸爸,即使有談,也是很簡短、小心翼翼。朋友跟我說,孩子講到爸爸時會批評爸爸,好像我的翻版,我還沾沾自喜覺得孩子好挺我,有一種覺得孩子有看到我辛苦的欣慰。
第一次意識到真的不能再這樣下去,是孩子手機上網事件。
我幫孩子辦了一支手機方便聯絡,因為怕他一直上網,所以並沒有讓他有網路,但是我卻發現他晚上不睡覺、偷偷在玩線上遊戲。我問他怎麼會有網路,他說爸爸給他易付卡,他有拒絕,但是爸爸就是要買。我質問他爸爸時,他爸爸居然說:是小孩跟他說「媽媽說她已經出手機的錢,媽媽叫你要出網路的錢」。
我們赫然發現,孩子居然已經大到知道如何鑽「大人互不溝通」的漏洞。
第二次是管教孩子時,孩子生氣跑出家門,幾個小時後都不見蹤跡,我打電話都不接,我超級緊張,心中有很多小劇場,擔心他會不會發生意外、擔心他會不會去找壞朋友、被騙走,還好後來是爸爸傳來簡訊跟我說,孩子在他那兒。
剎那間,我腦中想起當年教導
「合作父母課程」的老師說:
「合作父母是幫孩子多留一條路,
孩子在你這裡受挫,至少他還可以找對方。」
我思考著,我難道真的要孩子討厭爸爸? 特別是孩子越來越大,邁入青春期可能更需要爸爸的角色,我真的不應讓孩子捲入父母的恩怨。(延伸閱讀:給爸爸的照顧指南—爸爸不是媽媽不在時的代打,而是促成健康母嬰關係的要角。)
我開始練習不透過孩子傳話,溝通時盡量平穩與不要故意嘲諷,即使有氣也不要在孩子面前批評對方。這對我來說真的是修練的過程,因為我還是對爸爸的教養看不順眼,但是我跟自己說要忍耐、要尊重對方不同的親職教育方式。
剛開始調整時,爸爸也並沒有好的回應,交付時還是冷漠,但我跟自己說再試試看,畢竟我是為了孩子;而關係這件事真的很奇妙,當我不斷嘗試調整努力不要「吵」時,就像一個巴掌拍不響,好像關係真的有變好一點。
最讓我感動的是,某次我跟孩子吵架、他又跑去爸爸那裡時(青春期的孩子真是不容易教養),孩子回家後跟我道歉,說是他的態度不好,因為爸爸跟他說:「媽媽一個人帶你很辛苦,念你也是擔心你,不要一直頂嘴。」
我彷彿肩上放鬆了一些,
覺得育兒路上有被支持,
不是只有一個人。
這兩年,孩子上國中,我跟爸爸關係更鬆一些了,可以很心平氣和地討論孩子的狀況,我也開始可以跟孩子聊聊爸爸。孩子跟我說:「我以前真的很怕在妳面前提到爸爸,因為我知道妳不喜歡,我怕妳一不高興也不要我了,我不知道我要去哪裡。但是我很愛你們,謝謝你們現在可以讓我都愛你們,不用選一個。」看著孩子去爸爸家時,可以微笑的跟我揮手說再見,我知道我為孩子的努力值得了。(延伸閱讀:童話故事裡的教養智慧|被母職擊潰時,我們有機會蛻變成不一樣的自己)
當阿姨出現
當聽到孩子說,跟爸爸見面時多了一位王阿姨,我的心頭揪緊了,她會是孩子的後媽嗎? 我想從孩子口中探知一二,但又覺得自己應該忍住。在前夫的臉書上看到親暱照片,我知道是真的了……。我想,這也許是我的合作父母的新挑戰,因為我與孩子關係中,除了爸爸,現在還多了另一個阿姨……。
從「前伴侶」(怨偶)到「孩子的父母」的關係,
合作父母一詞的艱辛,真的不是用三言兩語就可道盡。
剛離婚時,雙方情緒都還很高張,我也真的難做到,但是謝謝經過時間的沉澱,我們都願意選擇慢慢放下仇恨、一起愛孩子。這一路雖經歷層層關卡,但是很高興我們已經往正確的目標邁進。
你可能還會想看…
「爸爸媽媽決定要分開了…」—夫妻離婚後,可以去哪裡去尋找給家庭的資源?
「爸爸媽媽決定要分開了…」—離婚後,夫妻雙方可以怎麼合作、共同育兒呢?
「夫妻面臨離婚,該怎麼確保孩子不受心靈創傷?」—這樣處理,可以幫助孩子感覺安全。
作者簡介
黃心怡、謝子瓔、劉于瑞、宋名萍、蕭丞芳(現代婦女基金會社工團隊)
我們是一群在法院第一線、協助過無數家庭紛爭的社會工作者。
除了看見家暴被害者的傷與痛,也看見施暴者的挫敗和心聲;我們發現家暴不只有一種面貌,因為家庭成員的因應方式,往往造就不同的結果。家事事件法通過、家事服務中心成立後,我們進一步走入面臨離婚、爭取監護權的家庭中,著手推動「未成年子女親子會面」的工作。
經過無數研習和討論,我們將工作中的行動研究和心路歷程,寫成文字紀錄、匯集成書,希望幫助面臨家庭離異風暴的大人及孩子們。